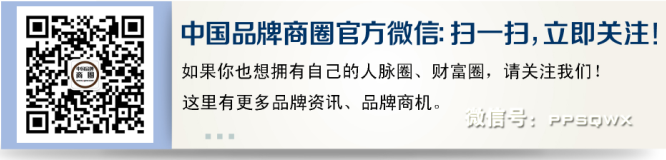摘要:他是中国最具理想气质的CEO,他是年轻人心中的企业家偶像。这一次,在《成功是和自己的较量:王石哈佛问道》中,他只愿和年轻人聊一聊人生。聊聊那些比成功这件事儿更重要而不朽的一切——关于理想与落差,关于选择与坚持。
还有法国的拉雪兹公墓,我当然也知道。为什么呢?我们20世纪50年代长大的人都有共产主义情结,《巴黎公社》最后那些遇难的抵抗的巴黎公社社员就是在拉雪兹公墓,在那儿有一道墙,他们最后顽强抵抗被俘的是在那儿枪决的。我是为看那座墙去的。
但中国的墓地为什么要把生死这样截然分开,并且在形象的外观上,弄得大家对它的亲近程度那么低呢?我觉得是一种对死亡的惧怕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在退化,实际上你要看中国古代的书,看春秋战国的时候庄子对死亡的态度。现在不知道我们怎么是进化到这个样子了,完全是回避死亡,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。
我也害怕丧失追求的动力
真善美,我是这样看的:实际上这就是对生命的态度。在成功之后,有时候突然你才认识你的缺点很多,你太自以为是,很多你认为讨厌的东西你自己身上都有,所以自以为是,以为自己就是绝对权威,绝对权威就是一言堂,你会发现你比别人强不了多少,我更想说是加入了阿拉善外界对自己的影响,要妥协这才是你的一个提高。当然主动妥协和被动妥协是有区别的,阿拉善是我主动妥协的,你不妥协你可以不当会长,不参加那个组织可以辞去会长,你就可以不受那个约束了。
说到完善,真的不敢说完善。哪儿完善呢?但是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有恶魔的一面,所以才觉得制度是重要的,你才觉得是需要约束的,首先约束的第一个就是自己,实际上我是不时地在物质面前挣扎的。当然,你想怎么可能?你就是做了几百亿元,你看我公司做到1000亿元我很兴奋,很多时候自己的家产都是几百亿元,你怎么能没有什么想法呢?当然会有一些想法。
但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。看你怎么去认识它,最基本的生活态度决定你到那里去了,但你也不会怎么样。这个是一直会有的问题,不是说我马上再有多少钱。什么叫生活态度呢?最起码要把握,就是你的生活已经是很好了,你想做什么事情也不是很困难,要让你的家庭生活较为满意,不能让他们很满意,较为满意你也做到了,那你现在的钱都要做公益,有更多的钱也会去做公益,这个状态你不会改变了。但是也可以这样说,是公司发展到现在这样决定的。刚才讲持续稳定的才开始,就要出现效率,作为管理团队就不是我一个人,他的收入待遇会越来越高,我也抱着期望,也希望这个越来越高,实际上我对自己约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,很担心我会失去控制,如果我现在的财富够我们家人两三代都用不完的话,那我现在就没有这种动力。
比如说现在有100多亿元,这是你的财产,难道你接下来剑桥也不去了,牛津也不去了,哈佛也不去了,不再看书了不再追求不再奋斗了吗?
要点不在这儿,剑桥还会去牛津还会去,但更多来讲你奋斗的压力就会少一点儿。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人,我不是。首先我是个物质主义者,物质主义者成不了思想家。我成为一个企业家,企业家无非是两种思维方式,一种首先变为自己,因为是有控制权,并不是说自己所有的都要有控制权,你的股权是60%,意味着60%代表的是财富,再一个更多代表的是表决权。作为我来讲我不要财富,不是我不要财富,实际上我表示我的一个信心,我不是靠60%、靠51%来掌控这个公司,我不是靠这个,有控股权是凭我的能力,这本身是自信心。
另外一个就是你突然钱很多了,会容易失去动力的,失去动力会怎么样?我们只能假设,难道你就不会去了吗?我不知道,因为财富多少它会起着根本的变化。另外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我的野心,就是个财富英雄者。我觉得和我部下关系是不大一样的,凭什么给你王石卖命?凭什么给你王家家族卖命?那不是,我是个创业者,是个创始人,但是你看到了,分的股票我放弃了,我和你们一样,如果那个股票我不放弃,现在我应该有一千万元。我不知道多少,那一千万元现在股价也就一个亿。说句不好听的话,现在一个好房子贵一点儿都上亿元了,但是我的尊严在什么地方呢?我的尊严就在我绝对不会挪用其他的钱去买我追求的房子。我不追求并不等于我家人没有追求,我觉得尊严是体现在这里。而不是说你钱多了就没尊严了,当然有尊严,当然还会接着去学习。你会完全不一样,因为钱多,我那时候讲钱就是个数字。但对我来讲钱不是个数字,多少钱它就是买个什么东西的,有多少钱能做什么事情的。
下一个目标
首先,我应该说做企业搞得好不好现在还在延续,大家目前认为好,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讲,30年、100年之后再评价现在都是过眼烟云,所以能不能好,能不能持续下去成为一种范例才是我现在应该在意的事情。像二战之后的索尼、丰田、松下这样,能不能像韩国的三星这样,在30年之后再评价,那时候才更准确一些。所以现在是不是这个企业就搞得很好,只不过现在它还在做,现在还能被大家认可,仅此而已。
第二个登珠峰,我来概括就是说登珠峰挺难,但你是作为一种爱好去的,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难。登珠峰首先就是实现个人那种野心,一般有你一种实现感,一种我能,你能吗?更多还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表现。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种兴趣,兴趣在这个地方。
第三个因为我自己对设计有一个设计,我设想到去哈佛学习,但我很想到大学进修一下,只不过是哈佛邀请了我。我原来有设想,我50岁到60岁就得登山,60岁到70岁的时候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到各处去讲演露面,这个基本就是说要退出这个舞台了,这已经不是你玩的舞台了,因为不是你愿意不愿意,抛物线它应该是往下走了。
另一个就是你个人的实现感,你个人如何是对你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个交代,更多是到大学里去,不是到那儿去讲演,像今天我讲完了拍屁股就走了。更多的学生是带有课带有分带有考试的,所以你要备课,要对他们负责任。所以原来我个人设计,60岁到70岁就是本人的设计。所以现在我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一年书了,现在也是受聘,试了一年之后,他们还继续再聘用我,又签了两年的合同。就是从今年到明年两年,讲企业伦理。现在是刚结束一个学期,也就是上个月,我刚刚接受光华管理学院的邀请,当然光华先是试聘的。我现在在哈佛,实际上就是个人修为。我总是说自己还要去哈佛进修两年,这样再去讲课自己更有点儿底。
所以没有怎么说登的第三个高山。但是我在哈佛的一年,确实觉得比登珠峰还难。刚才不讲了我说的几个阶段吗,第一学期是感到脑袋累,第二学期感到眼睛累。因为我已经开始正式听课,第二学期就是上午听课,下午在英语学校。因为那儿听课的全部都是上午课程,要读大量的资料,不像听讲座那么轻松了。当然不读资料你跟不上课,你要跟着一课一课那样听。如果不懂资料,你听课的时候,老师一看你,你就会低下头,怕他问你问题。
到了第二学期还是这样,到第三学期相对放松一些。但你要知道学习语言这是个工具,这不能说你语言过了关,你能用英文听能用英文讲了,这不是目的这是工具,你真正的是再去学习。我最大的体会是,原来很明确的东西,突然到那儿真正要学时发现很茫然,觉得这也想学,那也想学,又觉得这个是多余的吧,那个也觉得是多余的。也有点儿像刚选专业,万科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时候,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困惑。不像你说我就搞房地产,其他的都不做,我不知道应该选哪个。
比如说我现在听的最津津有味的就是《现代战争起源》。《现代战争起源》指的就是一战、二战、冷战,冷战结束之后,最重点的是讲最近30年。题目一开始就讲,你认为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倾向于和平吗?回答非常简单,民主国家更容易发动战争。不信,很简单,统计学上最近30年的战争全是美国发动的,它是一种方法论,来让你怎么来思考。
在那里你觉得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,这个才是开始。所以这是对我真正的挑战。登了两次珠峰我没感觉新生,不就是你沿着人家的路登上去了吗?但我多少有点儿感到在哈佛是真的新生。